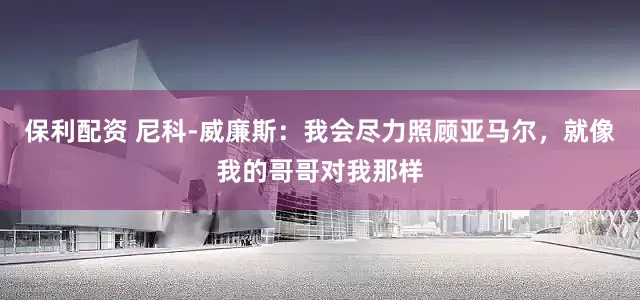听闻老同学仙游,悲痛万分,总想写一点东西,以为悼念,却因悲痛过分,茫茫然不知何处落笔稳赢配资,直到心绪稍微平静的今日。

我和自立兄相识,是在家乡秋山(禾山赤面峰)脚下的禾麓小学。
禾麓小学隔壁是当时的联保所(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)。学校和联保所大门前,各有一口池塘。池塘前是一堵围墙,墙外是一条从秋山上淌下来的小河。河水潺潺,蜿蜒曲折,流向不远的台岭乡南汶村。
河边荒草萋萋,杨柳阴阴,十分美丽。学校背后,则是一块土质悬崖,悬崖上有座“混凝土质”的碉堡,一条山路,绕过碉堡,直抵满是油茶树的山坡,通向湖塘村。平常这里幽静异常。
记得,那时自立兄好像已是禾小高年级的学生了,而我则刚进小学。
那一年,学校发生了一件高年级学生闹“逃学”的事件:有个老师,教学水平太差,但后台很硬,没办法,学生只好用“逃学”的办法,表示抗议。
在禾麓小学后山的油茶树林中,一个个矮小的身影穿梭着,用空心稻草,吸食着白色茶花花蕊中的“蜂蜜”,直到这堂课下课铃声响起,这群学生,才从山坡上下来,走进教室。
一来是这个老师教学水平的确太差,校长对他没有好印象,而他有后台,又不能动他,此时学生有意“逃学”,校长正好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借这个机会,整一整这个老师。
再加上自立兄的父亲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,在我们这一带很有声望,这个老师也拿自立兄没有办法,于是,此事便不了了之。而我却因此知道了萧自立的名号。

以后,自立兄离开禾麓小学,到县城上了中学,我们失去了音问,直到解放,他家被划成地主,他则成了地主崽子。又因为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,他则从县城被押回到布淌挨批斗。
其实,他的父母都不是他的亲生父母;他的亲生父母是河南某地的穷苦农民,他是遭“遗弃”而被现在的父母拾到的孩子。
在一次批斗他的时候,好心的知情人士告诉他这个信息,也向土改队作了汇报。土改队的工作人员觉得,不能将一个孤苦贫寒的人当地主,从此再也没有对他进行批斗。
然而他的亲生父母找不到了——连他的养母都不知道他生身父母的音信。他偷偷地告别了现在的母亲,离开布淌,跟随禾麓小学一位教会他拉京胡的老师,去了安福县的虎坑坞矿拾“坞沙”。
此后一段时间稳赢配资,我没有了他的消息。

后来,我从禾麓小学毕业,考上了永新中学。到永新中学后,我分在五班。初二时,班主任是陈少兰老师。
有一天,突然来了个插班生。经陈老师介绍,这个插班生竟然是和我在禾麓小学同过学,闹过“逃学”风潮的萧自立!
自此我们成了真正的同班同学了。
自立兄很有文艺才能,拉得一手京胡,会唱京戏,普通话也说得不错,而且善于演戏。
我这个人,政治上浑浑噩噩,一辈子无党无派,只在初中时入过少先队。
我记得,那时永新中学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是贺水镜老师。
有一次,贺老师领着少先队员去野营,我和自立兄都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那是一个秋天,我们来到了城郊的一块草坪上。离离荒草,镶嵌着经过修剪的圆顶小松树,就像黄色地毯上开着一朵朵翠花。美丽极了。
在禾麓小学时,我曾经学过一曲京剧,叫《梅龙镇》:搞文娱活动时,贺老师安排我唱这曲京剧,由自立兄京胡伴奏。我刚唱两句:“有孤王,坐至在梅龙镇, 想起了朝中的大事情”,就唱不下去了,只好停下来。

贺老师没办法,又叫:“大家欢迎自立同学自拉自唱一曲”。自立兄果然自拉自唱了一段京戏,赢得满场喝彩。
初中毕业后,我们都考取了永新中学高中,且同分在二班,班主任还是陈少兰老师。
此时,自立兄的文艺才能更加彰显出来了。他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,和贺家宾、刘世南等老师一起,演出过曹禺的话剧《雷雨》。
经历了“五八”年的大跃进,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我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季,奔向了人生命运的一大节点。
因为自立兄有文艺才能,他选择报考江西艺术学院,并获录取;我则在吉安体检时发现得了肺结核,不能参加高考,到我大哥工作的所在地淮阴治病并做了个代课教师。从此,我们再没有了相互的音信。
由于好友欧阳健的推荐,并获得时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徐若通、文学所两任负责人刘冬、刘洛同志的同意,我被调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,负责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的编纂工作。后来,又遴选作了政协江苏省八届委员会委员。

由于我在政协委员会上的一篇发言稿,引起了中新社记者陈光明的注意,作了报导,而《南方周末》又转载了这篇报导,因之自立兄发现了我,并且联系上了我。我真是高兴万分。
从此我们书信、微信往来,从不间断,仿佛又回到了童年,回到了中学的同窗时代,回到了彼此的前半生。
他从江西艺术学院毕业后,被分配到了江西龙南县,从事文化工作。
在龙南,他专注于客家文化的推广研究,因为成果丰硕,被遴选为县政协委员,并且担任了副主席。

不过我最关注和佩服的还是他对待他养母的态度:他退休以后,养母老了,身体不大好,又不想离开家乡,于是他把养母从布淌接到了永新县城,就医院附近,租了间民居居住。“一个60多岁的老人,精心照料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,不容易啊!”邻居们都赞叹说!
养母去世后,他又在布淌装修了养母居住过的三间老屋,摆放母亲的遗物和奉养先人的供桌。这是我与老同学刘茂珍到布淌亲眼目睹的。他布淌的近邻,纷纷称赞:“一个好人啊!”
我和刘茂珍学兄还去过他现在居住的地方——赣州。
在赣州,他引我们拜访了永新中学的校友陈光亮、甘二龙,还特别介绍我们拜访了校友颜定邦、陈月娥夫妇。
我清楚地记得,他给我们介绍颜定邦时的激动又带点骄傲的心绪:这是我们赣州稀土的发现者,是我们永新中学的光荣!那时,我还不明白稀土的发现对国家的贡献,而自立兄却关心国家大事,觉得这发现将影响国家的前途!
在赣州,我们还去过记载蒋经国做赣州专员时事迹的纪念馆;去过有名的郁孤台。在参观郁孤台时,自立兄不无感慨地吟诵着辛弃疾的千古绝唱:“郁孤台下清江水,中间多少行人泪?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,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余,山深闻鹧鸪。”

自立兄的传奇经历,犹历历在目;自立兄的音容笑貌、愁绪感慨犹栩栩如生,而人却已然仙游,岂不痛煞学弟。
倍悦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